《云起轩词序》
文廷式
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之也。其声多嘽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有清以来,此道复振。国初诸家,颇能宏雅,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词者,远继风骚,近沿乐府,岂小道欤。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宂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蒋鹿潭有沉深之思,成容若学阳春之作,而笔意稍轻,张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离于方罫者也。余于斯道,无能为役,而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三十年来,涉猎百家,搉较利病,论其得失,亦非扪龠而谈矣。而写其胸臆,则率尔而作,徒供世人指摘而已。然渊明诗云:兀傲差若颖。故余亦过而存之,且书此意,以自为序焉。
光绪壬寅十二月。
嘽chǎn缓:柔和舒缓。《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有二人焉,乘辂而歌……嘽缓舒绎,曲折不失节。”吕延济 注:“嘽缓舒绎,柔和之声也。”
柔靡:柔弱委靡。 宋. 范仲淹 《上时相议制举书》:“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
风云月露:《隋书?李谔传》:“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后即用“风云月露”指绮丽浮靡,吟风弄月的诗文。
红紫(红紫)
(1).红色与紫色。古代以青、赤、白、黑、黄为正色,红紫则是正色以外的间色。《论语?乡党》:“红紫不以为亵服。” 朱熹 集注:“红紫,闲色不正,且近於妇人女子之服也。亵服,私居服也。” 汉 扬雄 《法言?吾子》:“或问‘苍蝇红紫’。曰:‘明视。’” 李轨 注:“苍蝇间於白黑;红紫,似朱而非朱也。” 南朝 梁 刘勰 《文心雕龙?情采》:“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於红紫。” 清 曹寅 《孔雀》诗:“有时妬红紫,独立愁云天。”
(2).红花与紫花。 唐 韩愈 《晚春》诗:“草树知春久不归,百般红紫鬭芳菲。” 宋 韩维 《送孔先生还山》诗:“东风吹百花,红紫满岩谷。”
芬芳
(1).香;香气。《荀子?荣辱》:“白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橘柚芬芳。” 唐 韩愈 《重云李观疾赠之》诗:“穷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 老舍 《四世同堂》五二:“种菜浇花只是一种运动,他并不欣赏花草的美丽与芬芳。”
(2).比喻美好的德行或名声。 汉 崔瑗 《座右铭》:“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晋 葛洪 《<抱朴子>自叙》:“耀藻九五,绝声 昆吾 ,何憾芬芳之不扬,而务老生之彼务。” 唐 孟郊 《答卢仝》诗:“仰慙君子多,慎勿作芬芳。” 郭沫若 《蔡永祥》诗:“一瞬 泰山 重,百代颂芬芳。”
(3).犹纷纷。《敦煌变文集?丑女缘起》:“彩女嫔妃左右拥,前头掌扇闹芬芳。”《敦煌曲子词?酒泉子之一》:“金箱玉印自携将,任他乱芬芳。”
戒律
禁止教徒某些不当行为的法规。如佛教有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类。道教亦有五戒、十戒、一百八十戒等类。《百喻经?蛇头尾共争在前喻》:“如是年少,不闲戒律,多有所犯,因即相牵入於地狱。” 唐 杨炯 《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恨深负米,荣暨击钟,爰持戒律,思答慈容。” 宋 高承 《事物纪原?道释科教?戒律》:“ 汉灵帝 建宁 三年, 安世高 首出《义决律》二卷,次有比丘诸禁律。 魏 世 天竺 三藏 昙摩迦罗 到 许州 ,至 洛 ,慨 魏 境僧无律范,遂於 嘉平 中,与 昙谛 译《四分羯磨》及《僧只戒心图》,此盖中国戒律之始也。” 老舍 《牺牲》:“他必是一种什么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简单而又深密。”
(2).泛指其他成文或不成文的戒条。 清 陈康祺 《郎潜纪闻》卷六:“尝制圣门戒律八条,自警警世。” 柯岩 《从一个孩子看中国》四:“清规戒律,密如罗网。”
迈往
(1).超脱凡俗。 晋 王羲之 《诫谢万书》:“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羣辟,诚难为意也。” 宋 陆游 《贺叶枢密启》:“负沉雄迈往之略,躬英发绝人之姿。” 明 唐顺之 《答王南江提学书》:“夫兄雄俊之文,博辩之才,迈往之气,无一人不知之。”
(2).谓时光流逝。 清 曾国藩 《复刘霞仙中丞书》:“少壮真当努力,光阴迈往,悔其可追!”
(3).谓一直向前。 李大钊 《国民之薪胆》:“吾民惟一之大任,乃在迈往直前,以应方来之世变。” 闻一多 《雪》:“仿佛是诗人向上的灵魂,穿透自身的躯壳:直向天堂迈往。”
宏雅
正大而典雅。 汉 陈忠 《荐周兴疏》:“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宏雅,辞必温丽,垂於后世,列於典经。”按,宏,《后汉书?周荣传》引作“弘”。
迩来:最近以来
(1).从某时以来;从那以来。 晋 王嘉 《拾遗记?蜀》:“及 春秋 时,有 子韦 、 子野 、 裨灶 之徒,权略虽险,未得其门。迩来世代兴亡,不复可记,因以相袭。” 唐 白居易 《念金銮子》诗之二:“忽然又不见,迩来三四春。” 宋 欧阳修 《归田录》卷二:“ 太宗 时,有待诏 贾玄 ,以棊供奉,号为国手。迩来数十年,未有继者。”
(2).犹近来。 唐 韩愈 《寒食日出游》诗:“迩来又见桃与梨,交开红白如争竞。”《水浒传》第一○一回:“迩来边庭多儆,国祚少宁。” 鲁迅 《书信集?致陈浚》:“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
辄:◎ 总是,就:动~得咎。浅尝~止。◎ 古代车箱两旁的板上向外翻出的部分,像耳下垂那样。◎ 仗恃胡作非为:“甘受专~之罪”。
照天腾渊之才:?
溯:◎ 逆着水流的方向走:~流而上。◎ 追求根源或回想:回~。追~。上~。追本~源。
涵:◎ 包容,包含:~蓄。~容。~养(a.蓄积并保持,如“~~水源”;b.指修养,如“他很有~~”)。包~。蕴~。海~。◎ 沉,潜:~泳(水中潜行,喻深入体会)。~淹。~濡(浸渍,滋润)。◎ 公路或铁路下面通沟渠的管道:~洞。桥~。
磅礴pángbó:充满于…的。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庄子》
八极:八方极远之地。《庄子?田子方》:“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淮南子?原道训》:“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 高诱 注:“八极,八方之极也,言其远。” 唐 李白 《大鹏赋》:“余昔於 江陵 见 天台 司马子微 ,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鲁迅 《南腔北调集?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杜威 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 白璧德 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 中国 的呵斥八极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吗?”
甄综(甄综)zhēn zōng:综合分析,鉴定品评。
百代:指很长的岁月。 汉 王充 《论衡?须颂》:“《恢国》之篇,极论 汉 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晋书?阮种传》:“德逮羣生,泽被区宇,声施无穷,而典垂百代。” 唐 韩愈 《禘祫议》:“其毁庙之主,皆藏於祧庙,虽百代不毁。”《儒林外史》第一回:“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窘:◎ 穷困:~厄。~乏。~苦。~困。~迫。~促。~急。◎ 难住,使为难:~况。~态。~相。~境。
若:好像
囚拘
(1).囚禁。 汉 刘向 《新序?节士》:“[ 关龙逄 ]立而不去朝, 桀 因囚拘之。” 唐 萧颖士 《仰答韦司业垂访》诗之四:“岂知 晋 叔向 ,无罪婴囚拘。”
(2).指被囚禁的时期。 清 刘大櫆 《祭望溪先生文》:“其治三《礼》,半在囚拘。死而后已,其生不虚。”
(3).受束缚。 唐 韩愈 《同冠峡》诗:“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羇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
(4).比喻受束缚的人。 唐 元稹 《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
(5).囚俘,俘虏。 唐 柳宗元 《铙歌鼓吹曲?高昌》:“ 麴 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臣 靖 执长缨,智勇伏囚拘。”
远继风骚:?
岂:◎ 助词,表示反诘(a.哪里,如何,怎么,如“~敢”,“~堪”,“~可”,“~有此理”;b.难道,如“~非”,“~不”,“~有意乎”)。
欤:助词,表示疑问、感叹、反诘等语气。
小道:儒家对宣扬礼教以外的学说、技艺的贬称
(1).礼乐政教以外的学说;技艺。《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何晏 集解:“小道谓异端。” 刘宝楠 正义:“《周官?大司乐》注:‘道,多才艺。’此小道亦谓才艺。 郑 注云:‘小道,如今诸子书也。’ 郑 举一端,故云‘如’以例之。” 唐 孙过庭 《书谱》:“ 扬雄 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 元 辛文房 《唐才子传?陈上美》:“俱以一咏争长岁月者亦多,岂曰小道而忽之。” 陈毅 《题<围棋名谱精选>》诗:“棋虽小道,品德最尊。”
(2).邪路;非正途;非正式的途径。《谷梁传?隐公元年》:“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 北齐 魏收 《前上十志启》:“间有小道俗言,要奇好异,考之雅旧,咸乖实录。”《儿女英雄传》第十一回:“小人从前原也作些小道儿上的买卖,后来洗手不干。” 徐怀中 《西线轶事》二:“她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正式宣布,说不让去,是小道透露出来的。”
(3).道士或道姑的谦称。《水浒传》第一回:“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 唐 洞玄国师 封锁魔王在此……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镜花缘》第四五回:“忽见有个道姑走来道:‘女菩萨休要害怕,小道特来相救。’”
(4).小路。《儿女英雄传》第四回:“这东南大道岔上,下去有条小道儿。”
朱竹垞: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曾参加纂修《明史》。
宗:◎ 家族的上辈,民族的祖先:祖~。~庙。~祠。◎ 家族:~法(封建社会以家族为中心,按制统远近区别亲疏的制度)。~族。~室(帝王的宗族)。~兄。
◎ 派别:~派。禅~(佛教的一派)。◎ 主要的目的和意图:~旨。开~明义。
◎ 尊奉:~仰。◎ 为众人所师法的人物:~师。◎ 量词,指件或批:一~心事。◎ 姓。
宂漫:亦作“冗漫”。繁琐芜杂;散漫。 清 叶廷琯 《吹网录?<史通削繁>序误》:“ 河间 纪文达公 有《史通削繁》一书,删去 刘子元 原文冗漫纰缪者。”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六章第二节:“[ 沉寿卿 《三元记》]结构冗漫,后半尤弱。”
祖祢(祖祢): (1).祖庙与父庙。《周礼?春官?甸祝》:“舍奠于祖祢,乃敛禽,禂牲,禂马,皆掌其祝号。”《史记?孝武本纪》:“鼎宜见於祖祢,藏於帝庭,以合明应。”
(2).先祖和先父。亦泛指祖先。 汉 蔡邕 《鼎铭》:“乃及 忠文 ,克慎明德,以服享祖祢之遗风,悉心臣事,用媚天子。”《旧唐书?段文昌传》:“以先人坟墓在 荆州 ,别营居第以置祖祢影堂,岁时伏腊,良辰美景享荐之。” 宋 文天祥 《<告先太师墓文>跋》:“余始至 南安军 ,即绝粒为告墓文,遣人驰归,白之祖祢。”
(3).本源;起始。 清 徐釚 《词苑丛谈?三百篇为词祖》:“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岂非《三百篇》实祖祢哉。” 章炳麟 《訄书?订文》:“数字之义,祖祢一名,久而莫踪迹之也。” 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所谓徽调、汉调、秦腔等等,都是代表的地方戏,先于皮黄而出现,而为其祖祢的。”
视:看待
仇雠(仇雠|仇讐) chóuchóu
亦作“仇仇”。仇人;冤家对头。《左传?哀公元年》:“[ 越 ]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荀子?臣道》:“爪牙之士施,则仇讐不作。” 唐 刘商 《胡笳十八拍?第十五拍》:“不缘生得天属亲,岂向仇讐结恩信。”《旧唐书?张浚传》:“忘廊庙之威重,结藩屏之仇雠。” 清 毛秀惠 《钱塘怀古》诗:“自愿苟安增币帛,谁抒孤愤报仇讐。” 鲁迅 《故事新编?铸剑》:“他决心要并无心事一般,倒头便睡,清晨醒来,毫不改变常态从容地去寻找他不共戴天的仇雠。”
斯:◎ 这,这个,这里:~人。~时。以至于~。◎ 乃,就:有备~可以无患。◎ 劈:“墓门有棘,斧以~之”。◎ 古同“厮”,卑贱。◎ 古同“澌”,尽。
庸:◎ 平常,不高明的:平~。~医。~言。~俗。~人。昏~。~主(平庸或昏庸的君主)。~夫。~暗(平凡,愚昧)。~~碌碌(没有志气,没有作为)。◎ 需要:无~细述。无~讳言◎ 岂,怎么:~讵(岂,何以,怎么,亦作“庸遽”)。◎ 中国唐代一种赋税法:租~调。◎ 功劳:~绩(功绩)。◎ 古同“佣”,雇佣。
谬:◎ 错误的,不合情理的:荒~。~论。~传(chuán )。~误。◎ 差错:失之毫厘,~以千里。
笼绊:lóng bàn羁绊,受牵制。《北史?卢思道传》:“势利货殖,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去。”
盖:◎ 有遮蔽作用的东西:~子。锅~。瓶~。膝~。天灵~。◎ 伞:雨~。◎ 由上往下覆,遮掩:覆~。遮~。掩~。~浇饭。◎ 压倒,超过:~世无双。◎ 方言,超出一般地好:这本书真叫~!◎ 用印,打上:~章。~戳子。◎ 造(房子):~楼。翻~。◎ 方言虚词(a.发语词,如“~闻”;b.表大概如此,如“~近之矣”;c.连词,表示原因,如“有所不知,~未学也”)。
俊爽:英俊豪爽;人品高超,性格豪爽
笔意:书画、诗文中表现的作者的风格、意趣。指书画或诗文所表现的意态情致。《新唐书?魏徵传》:“ 叔瑜 善草隶,以笔意传其子 华 及甥 薛稷 。” 明 刘基 《题富好礼所畜<村乐图>》诗:“想应临搨出秘府,笔意精到世罕俦。” 清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卷二:“ 王沂孙 《水龙吟》……笔意幽冷,寒芒刺骨,其有慨於 崖山 乎?” 徐迟 《井冈山记》:“同行人特地指给我看其中的一条标语,字迹秀拔,纵横吞吐,写得极好,大有 毛泽东 同志的笔意。”
方罫
(1).指棋盘上的方格。《文选?韦昭<博弈论>》:“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 张铣 注:“罫,线之间方目也。” 清 金农 《与谢山人夔池上弈》诗之一:“方罫楸枰布势迟,钩连小刼动偏师。”
(2).指整齐的方格形。 李斗 《扬州画舫录?草河录上》引 清 马曰琯 《毕园词》:“废池縠,野田方罫,著眼都如画。”
役:兵役,劳役
搉què : 通“榷”。商讨,商量。
扪:(扪)mén 按,摸。
龠:yuè古代乐器,形状像笛。
胸臆:xiōng yì心中所藏。
徒供世人指摘而已:(指摘:挑出错误,加以批评。供:gōng准备着东西给需要的人应用
)只是留给人们挑出错误并加以批评。
兀傲差若颖:晋 陶潜 《饮酒》诗之十三:“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兀:wù,高耸特出的样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兀,高而上平也。”兀傲:高傲,倔强,孤傲不羁。差:chā,略微,比较。颖:才能秀出,聪敏。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
吴梅的《曲学通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锺书的《谈艺录》等。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其中不乏像钱锺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第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第四是代表2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陶渊明,字元亮,或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著名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渊明从小就 “猛志逸四海”,对国家社会胸怀大志,立下“澄清中原”的大志。然而渊明年幼时,家境即已败落,身处乱世,有志不得伸,他只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几个不高的小官职,且时间皆不长。后来,灵魂不卖的陶渊明挂冠解印而归回田园,写下《归去来辞》一文以见其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怀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陶渊明为官的结果,获得的是苦痛与烦恼,因他“质性自然”的人事的束缚不适合他。抱负不得施展,又不肯与黑暗的世族社会同流合污,便于四十一岁那年弃官而去,从此开始他后半生的隐居生活。
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陶渊明诗歌现存120多首,有多种题材,其中最主要的是田园诗和咏怀诗。陶渊明的后半生长期活动在百里之内的农村,接触的多是田野村夫,议论的多是稻麦桑麻,过着平淡自然的贫士生活。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为他的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样,将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作为重要的审美对象来描绘自然就成了陶渊明诗歌的主要主题。“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每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不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明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①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可以概括为:
一、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爱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不错的,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其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我们很难在陶诗里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甚至连形容词都很少用,一切平平淡淡,只是白描,朴朴素素。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和陶渊明为人一样。因此陶诗读来韵味隽永,越读越觉得它美。
1. 清新的笔法。这与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形象模糊、晦涩难解、淡而寡味的玄言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陶渊明刻画田园山水,绝不追求华丽的的语言与表面的形似,而是随意点染,清新自然,而有无尽的神韵。试着《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会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
纷纷士女,趋时竞逐。 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在春天美丽的原野上,花木盛开,春各送暖,农夫农妇们为赶农时,纷纷下田,女的一早就去采桑,农夫干脆就夜宿在田野里。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欢乐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农作本来很很辛苦,但在作者来看,却是很美,一片清新自然,这也反映出陶渊明淳朴自然的性情。《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少。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渔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陶渊明逃离樊笼、获得自由、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他终于从“尘网”中解脱,就像鸟归山林、鱼回深池一样快活地长嘘了一口气。诗人不厌其详地罗列景物,“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②,形象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摆脱尘俗归返自然的这一特定环境中无比欣慰的心情。中间一节写景,“方宅”以下四句的清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已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对这些景物的描写,无不饱含着诗人对乡村的亲切依恋之情。,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束“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2.细腻的描写。陶渊明的田园诗植根于田园生活,他对田园生活的切身感受,融化在诗歌之中,最平常的一草一木,在他细腻描写下,都显示出无限的生机,构成一幅幅美丽的乡村图画。我们看他的诗: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之五)
诗中的意思是:扶着拐杖,从崎岖弯曲的山间小路回来,先在山涧小溪中洗一洗走得发烫的脚。然后斟满一壶酒,宰杀一只鸡,请来邻居,痛饮几杯。太阳下山了,就用火把照明,只恨夜太短。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如此生活情趣,又如此的诗意盎然。这首诗展示了浓厚的生活情调,表现了陶渊明对田园美和田园生活的敏锐观察力。他善于挑选富有诗意的题材,并通过细腻的描写,给人以美的享受。“此诗言还,不特章法完整,直是一幅画图,一篇记序。”③
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不少的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劳动,对一士大夫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诗人已认识到劳动在其是必要的,他对躬耕生活有了感情,并和农民之间有了经常性的交往: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他尝试了,这就很了不起的。同时其诗中还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心理上的安静乃至安乐。
3. 质朴的的语言。陶渊明的诗歌能千古流传,与他语言的质朴关系很大。陶渊明独特的生活经历,朴素的农村生活和平淡的田园景色,要求尽可能采用近似“田家语”的朴素的语言和白描手法,从而形成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达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效果。陶渊明的田园诗,农家生活气息浓厚,又体现了“贫士”诗人自己的性格。试看他的《移居》第二首诗: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诗酒相和,欢聚言笑,经纪衣食,不忘力耕,平淡、枯燥的乡间生活,在他笔下,却如此富有诗意。他并没有雕词琢句,裁云绣月,用的只是朴素的口语化句子,如实写来,他的诗篇看来古朴无华,读起来却琅琅上口,又如“平畴交远风,良苦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用朴素精炼的语言,逼真地描绘了自然景物。吟读此诗,仿佛眼前展现了一片广阔的田野,清风徐来,绿油油的庄稼碧波荡漾,生意盎然。
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如何?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他们的旧巢以及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里是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语言浅显平淡、质朴自然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之一)“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
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③十分精辟,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言:“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④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之三》)“蔼蔼堂前林,中厦贮清阴。”(《和郭主簿》之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十分精彩,不可更易。
二、情、景、理交融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是至关重要的,而情又是最为重要的。离开情的景就是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昧”的空理,景和理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陶诗在处理这一关系时,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
1.陶渊明并不是只有如前所述的以平淡自然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些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束说:“惜哉剑术疏,奇动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两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曾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⑤这首《读山海经》是陶诗情景交融因景就情感情较为强烈的代表作。
2. 在陶诗中,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水都包含了强烈的思想感情。他作诗无意于模仿山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统摄。在南山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
《拟挽歌辞》(之三)也是情景理三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呜,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
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写作者预想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前两句起兴,“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点明时间在秋天,九月乃晚秋,已经下霜,一早起然后说人皆有一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著:死了就别说什么了,不过是将形体托于山陵之中,回归自然罢了。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一诗勘破了。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述景比兴,衬托出萧条气氛,然而诗中又以旷达自慰,显出陶渊明一贯的通达的人生观,也算是曲终奏雅了。
同类诗中较具代表性的还有《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记叙了躬耕南山种豆劳作的情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是总括初始归耕的情况,在南山下种豆,但因为疏于耕作,豆苗长势并不好。这里似含有作者的无奈,也属自我调侃,说明作者的豁达。一大早下地锄草,月亮高升才归家,但还是免不了“草盛豆苗稀”,越发证明疏于耕作。前四句是述事,也是用典。《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宝贵何时。”作者走在农田中踩出的小道上,因草木茂盛,夕露已下,沾湿了衣裳。这两句写得极形象,非亲与躬耕者不能描绘。初始耕作,虽然辛苦,成绩也不算好,但仍然切盼最终能亲见有所收获。这也非亲与耕作者不能道出的。这首全属写实,展读之下,一位初始亲历农耕的隐者形象就活现在读者眼前。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盛赞此诗曰:“览渊明此诗,相与太皇。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所愧者多矣。”该诗明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歌咏自己的人生理想;明之写田园之景,实之都是在渲泄作者自身的情感,即对和平安宁、恬静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喜爱和对污浊喧器、虚伪欺诈的上层社会的厌弃。
3.陶诗又善于寓情于理,把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形象化,把诗情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因而给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觉。来,寒气袭人。这个时候,亲旧就要送我往村外的墓地了。四周而望,全无人居,只见坟头丛立,在荒凉空旷的坟地里,马到成功儿也觉得不自在,仰天而鸣,其声划破天空,于是感到风儿也极为萧条了。灵柩下到墓室,一经关闭墓门,千年之间,便不再能见到人间阳光了。这是多么凄伤啊!但是,无论贤愚,都不能逃脱这一劫。原先相送的人,不久已还原正常生活了,亲戚或者馀有悲恸,一般的人们早已歌于路途了,死算得什么!
且看《饮酒》(之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真有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器的干扰。“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它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的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外,还有什么可以追求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和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都能体现出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过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筌,其谁辨之。”《饮酒》(之五)这首诗,我们无法说是田园诗还是咏怀诗,因为诗中景、情、理水乳交融,互相渗透,互相衬托,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能领略到不同的奇趣,享受到无尽的美。
从诗歌渊源关系中说,陶渊明有继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语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中包含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于陶渊明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一个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有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的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陶渊明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辟的典故。他的诗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的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陶渊明文学成就,特别是他的田园诗,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他的田园诗,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反映了他的出仕与归隐,希望与失望,痛苦与欢乐的思想矛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生逢乱世、怀才不遇的封建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感情,即使退隐以后,也并未忘情政治,心情并未真正平静下来。他的诗文,平易朴实,清峻自然,淳厚有味,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精炼,深入浅出,在当时崇高雕琢,追求形式,骈俪盛行的时代,他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创作出大量质朴优美,生动活泼并富有情韵的作品,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他的诗歌均饱含着浓郁的情感,又情景事理水乳交融,做到了情景、事理和谐统一,开辟了古典诗歌的一新境界。
注释:①转引自明·黄彻《溪诗语》卷五
②引自黄文焕《陶诗析义》
③引自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④引自苏轼《与苏辙书》
⑤引自元好问《论诗绝句》
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言:“……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4月第1次版
(2)《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中国古代文学读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合编)
(6)《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罗宗强陈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0年版
(7)《陶渊明集》郭建平解评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年9月第1次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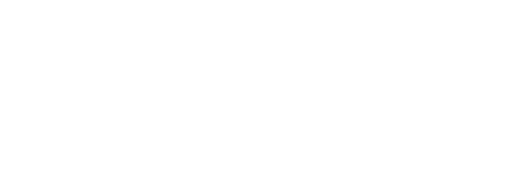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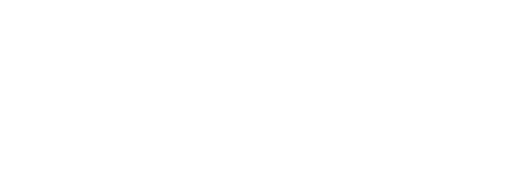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比乐号的签约作者“诗槐”
本文概览:《云起轩词序》文廷式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之也。其声多嘽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迈往之士,无所用...
文章不错《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 百度网盘》内容很有帮助